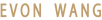|陶瓷的肖像計畫,東京的女老闆(二)
Cacao Mag 專欄|2021|圖文:Evon
關於專欄的自我介紹是這麼打的:「為了搞懂這個世界,或是自己,在東京手持啤酒,跟陌生人聊天,開始了陶土寫生計畫。」這都是真的,還記得有一晚我在涉谷和朋友拿著700ml的大玻璃杯,裝著滿滿的生啤一口都還沒喝就得趕終電(末班車)回家,索性就帶著啤酒搭上電車,被路人直直看著,對上了眼只好用日文問他:「要不要喝?」「一起乾杯吧~」沒想到大家還真的喝了起來,一大杯啤酒在車廂內傳來傳去,繞一圈就喝完了。
那個晚上應該是「花金 hanakin」吧?像花一般的金曜日,週五晚上的日本人特別放鬆,這些喝完酒的陌生人,有的在我拍照時亂入我的底片,有的加了好友吃了幾次飯,還有一位成為我研究計畫「從對話到作品 – 東京的女老闆們」的受訪對象。

我不是本來就會跟街上的人聊天的,可以說是不太擅長
剛搬到日本的前半年,我是一個還沒拿到簽證在學語言的學生,也不確定幾個月後能否考上研究所,每天往返語言學校與寄宿家庭,看似愜意旅行般的日子,卻也對接下來的一切完全沒把握。
別說申請銀行帳號,我連手機門號都辦不了,當時預付sim卡的選擇不多,也不想隨身帶著一台wifi機,於是就過著半年沒有手機門號也沒有行動網路的生活。如此的不便或許開啟了一些冒險,還有許多的緣分,到了今天我還是常常懷念起那些在涉谷忠犬小八銅像旁,各種等待會面的時刻。

那年九月,從仍暑氣難耐的台灣起飛抵達東京,我住進學校安排的寄宿家庭,一棟位於調布郊區兩樓的日式木造建築,有一位日本媽媽Yukiko、五歲的兒子Ryota,還有一隻年邁的瑪爾濟斯,我用生硬的日文語調自我介紹,不會講英語的Yukiko便用片假名寫下我的名字壓在餐桌的玻璃墊下,我的名字從怡方變成Evon再變成了イバン i-ban(正確應該念做イファン i-fan,不過在這個家中就將錯就錯的叫イバン了…),住在二樓一間窗戶外是菜園的小房間,空氣很好,冬天下雪時要用煤油暖爐,從家裡步行十五分可到京王線的小車站「柴崎」,轉車搭急行大約40分鐘抵達涉谷車站,再步行十五分鐘(如果沒有被中途經過的幾間車站百貨櫃位給吸引耽擱),沿途穿越複雜的施工中的暫時通道後,終於到達涉谷某辦公大樓在27樓高的語言學校。
教室說是景觀餐廳也不為過,往下看有代代木公園的綠意盎然、六本木之丘的都會現代、也有東京鐵塔的紅與白。如果天氣很好,還隱約能看得到遠方的富士山。比起準備升學考試,學校更著重於日本文化體驗,學生大多來自歐美國家,很多正值升大學前的gap year,每週五學校都會有新的同學加入、結業的學生離開。大家總是來來去去,午餐時面對不同日文程度的同學們,反倒像是身處紐約,用不同口音的英文交談著。

上課時花了很多時間練習會話,我因為漢字的優勢被分入中高階班,卻跟不上這群熱愛日本動漫弟弟妹妹流利的嘴巴,在這裡二十四歲的我幾乎算是大齡學生了,課堂上大家幾乎要搶著發言,我卻常常傻笑開不了口。來自比利時的金髮妞用流利的日文啪拉啪拉地更新每週約會進度,日文老師總是皺著眉頭邊微笑聽著,想當記者的法國美女邊擦口紅,邊分享著她應徵新宿機器人餐廳時的經歷、智利滑板弟發表在公園才能學到年輕人真正用的日文的宣言,接著說他想退課⋯⋯。透過各種超乎預期的分享,我才發現原來在這裡學習日文的同時,也在學習透過語言解開對他人的好奇。
於是白天在教室讀書,晚上在居酒屋見世面的日子持續進行,我變得越來越會跟陌生人聊天了
我以「笨蛋外國人」做為開場白,在人生地不熟的東京都交朋友。最常聊天的對象,除了那些坐我旁邊喝到臉紅紅而胡言亂語的日本大叔之外,就是親切的老闆娘們。無論是散步經過的雜貨店、美容院,或著吃過一次便念念不忘的家庭料理店,每間店都有一位風格獨具的女主人,她們無視日本社會的常規,不穿套裝、窄裙、高跟鞋,在自己裝修佈置的空間裡,經營一片天地。
我常在午後排滿大小展覽的行程,從涉谷走到青山,從六本木搭車到銀座。因為手機沒辦法用Google map,所以要在出發前將附近的藝廊排好順路、畫好地圖。從銀座一丁目走到七丁目,一個下午連看六七間以上的藝廊展覽,繪畫、攝影、雕塑到新媒體創作,畫廊巡禮就是我的散步健行,包包裡也沒忘記帶好餅乾充飢。
時髦的銀座大街上有藝廊、巷弄裡的舊大樓中也有藝廊,我就在這之間認識了金井女士(封面照背影者)
那不是一間醒目亮眼的畫廊,沒有窗戶、沒有音樂、空氣安靜的有點厚重,牆壁看得出頻繁補土、油漆的痕跡。那天正展出東京藝術大學雕塑系學生的創作,層架上的小作品,不是特別精緻卻保留趣味的手感,穿著深色套裝的老闆娘從角落走向我,鮑伯短髮和有點糊掉的黑眼線,乍看有點兇的樣子。她用一長串日文介紹我眼前的作品,請我拿起來看看,我聽不太懂但還是乖乖拿起作品,眼睛對準小洞,霎時間彩色絢麗的世界,在我眼前聚集後開展,不小心驚呼出聲。手裡握著的奇怪小裝置原來是一件萬花筒。綜合百元商店的現成物,與手工焊接的工藝與繪圖,有點童趣的風格與親民的價錢,讓我和朋友當場購入了兩件萬花筒。
意外地在畫廊買了作品,沒想過買的會是萬花筒,老闆娘聽我從台灣來的正在準備多摩美術大學院的考試,約我同萬花筒作家(是個一年吃287份咖哩的漂亮女生)一起吃飯,自從我跟老闆娘在台灣料理店喝完一瓶紹興酒之後,彷彿通過了什麼台灣女孩好棒的認證,每次來畫廊看展完她都會約我喝個幾杯再回家,這間畫廊就像她一樣,不因客人的身份有差別的對待,充滿修補痕跡的牆面似乎讓空間變得真實,她總是認真傳達作家的個性,也專心聆聽別人分享的日常。
幾個月後,我如願考進了多摩美。當我決定要做東京女老闆的陶瓷肖像計畫時,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對象,就是金井女士。因為,我們雖然認識了一年多、喝過好多酒了,她卻還是一樣的神秘,連年紀也不願意透露。當我慎重地帶著訪綱及陶土來到畫廊,我像初次見面般透過她說的人生故事,想像她的形狀。
「黑色的衣服、白色的四角空間,
畫、明信片、紙張、瑣碎的工作內容,
攝影學校、廣告公司、想幫助的藝術家們,
沒辦法丟棄的照片、越來越溫柔的自己。」
訪問時我們坐在畫廊後方的小房間,櫃子中擺滿資料夾及歷年來的展覽文宣,她說工作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處理這些瑣事,我邊聽邊將土拍打成一片片疊起,她離開男性主導的廣告企業決定自立門戶經營畫廊已近二十年,沒有員工,每週只休息一天,公休日會跑到大老遠的美術館看展,平日就趁開店前逛一圈銀座的藝廊,日復一日。雖然沒聽她說過超愛藝術之類的話,但每次聽她討論作品有不有趣時嘴角上揚的樣子,都覺得她是真心喜歡著這份工作。

我回到工作室開始實驗材質,很直覺地畫了草圖,由黑漸層到白色的紙張疊成一座立方體,是她的工作空間,也像她的人,有包容某種殘缺的能力。為了呈現足夠脆弱的薄度,我嘗試用各種布料與紙張浸染泥漿後燒製,最後選了廚房紙巾,這麽瑣碎又日常、這麼消耗又用完即棄。我撕下一張又一張紙巾浸入泥漿桶內,那是粗糙黑泥製成的泥漿,將紙巾的正反面都吸飽泥漿後靜置陰乾,每完成一張紙巾,我就在黑泥漿中加入一匙細緻的白瓷漿,再將新的紙巾浸入泥漿,如此反覆,像是撕下每天的日曆,再一一寫上日子的重量,待水分蒸發後,這些紙巾漸漸變得輕盈。

疊起一層層的瓷漿薄片,直到底層無法負荷重量,我的動作像堆疊撲克牌塔般的小心翼翼地,憋著一口氣,雙手捧著作品放入窯中。經過一千兩百多度的燒製,泥漿中的紙巾灰飛煙滅,整體高度只剩一半。於是我在燒結的土上繼續疊上薄片再進窯燒製,反覆著進窯和出窯。由黑泥漸層至白瓷,在我想像裡,底層的黑色是火燒後的照片,角落斑駁破碎,過去的日子和倖存的記憶在堆疊與消逝間平衡。而頂端的白得足夠純淨,在角落靜靜雕出金井女士的名。

當這系列作品完成後獲得學校補助,在銀座藝廊舉辦我首次個展,展覽空間在一樓馬路旁,採光良好的落地窗前,可以看見展台上寫著金井章子與她所經營的畫廊名稱。有位看展的中年男子來回多次看著那展台,說他常去她的畫廊看展,但他表情甚是疑惑,問我:「她是像這樣子的嗎?」

金井女士在上班的空檔特地繞過來看,她是我訪問對象中唯一從事藝術工作的人,我緊張地等待她的感想,她微微偷笑地說:「對,我其實是這樣細膩的。」
在後來好多次的飯局裡,她總是有點得意的跟朋友分享我為她做的作品,她的畫廊成為我在東京展出合作的空間直到今日,謝謝陶土寫生計畫(或著謝謝那瓶紹興酒?),讓我在這陌生的城市中多了一處居場所,也讓我對不了解的世界又多認識了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