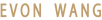|她和她的房間
展覽|部屋六畳|2020|文:吳思薇|攝影:Sabrina

她和她的房間
一覺醒來,看見陽光散漫而花正開,她打開窗戶輕巧地避開花瓣替植物澆水,她的窗台上種滿了龜背芋、含笑花、鹿角蕨、天使蔓綠絨、桂花和各種茉莉。泥土上有土偶、吊掛著的兔腳蕨還有盛開的梔子花,在太陽底下挺著枝幹,朝氣勃勃地散出草木花香。這是只屬於上午,太陽大到彷彿連時間都停止運作的時刻。
這是一八年後王怡方搬回台灣的她的房間。
如果想再靠近一點,去接近那個在東京涉谷八王子多摩橫須賀出沒的她,有幾個場景恐怕必須要筆記下來。
-
在多摩美術大學裡的圖書館,是的,那個伊東豐雄蓋的圖書館。
圖書館的地面層東北方,有一個角落,擺放了幾張一坐進去就使人陷下的高椅,你可能會在那裡見到她,蜷著身體的她無視於時間的轉速,正在用了一整個夏天的時間,奢侈地看電影,一部接著一部。她看Cult片大師亞歷山卓·尤杜洛斯基的變態《聖山》和《鼴鼠》。看高達眼裡最美麗又最危險的安娜,青春的身體和有邪的笑容。看伊丹十三《蒲公英》中風流無度的役所廣司和女人開房間吞生蠔、用唇齒傳遞生蛋黃。看黑白的小津和他永遠的處女原節子。而在危險野蠻的90年代,蔡明亮拍下還是美男子的陳昭榮,在無處不霓虹的西門町騎著速克達狂飆街頭。也不要忘了北野武的膠卷裡的北野武,是不可能更浪漫的男子漢。
看戲的或許都是傻子,痴迷的她止不住眼淚打濕臉頰。笑,就要哈哈大笑,就要笑出聲來,就要笑到流淚。她不是學究般的戲迷,沒有留下太複雜的筆記,只是記下那些心臟有點刺痛的時刻。
這是當工作室窯廠關閉,不能做陶的時候,她看電影。
-
近午夜的十一點鐘,只剩幾台腳踏車零落的停在校門口,剛被管理員好說歹說才從工作室請回的她,把車鎖解開跨上座椅才要回家。每次都要到了這個時候才發現自己原來那麼累,用最後的一點力氣踩著踏板爬過山的斜坡,腦袋裡轉了一下要去便利店帶一碗蔬菜湯和炸雞串回家,正所謂便利店人間。一個人住除了沒什麼好理由開伙,實際上是沒力氣。她的冰箱裡只有冰淇淋和啤酒,在那個甚至沒有網路、塌塌米六帖大的房間,剛滿25歲的她,一回到家就打開啤酒,翹開冰淇淋,好不容易吃完才終於回神,房間真的太小眼前就是穿衣鏡,在沒有網路只有音樂的房間裡,看著鏡子的自己就不小心聽著音樂就跳起舞來,跳累了,就睡了。
-
日間,她把頭髮紮成球狀,頭髮放下很難工作。右手執起鐵鎚敲碎土塊,然後把碎裂的土塊都攪入水裡、製成泥漿、過篩一次、兩次、三次,等著泥水相容成牛奶狀的質地,再舀入石膏模裡,繼續等待,無論耐不耐煩,都要等時間過去,泥漿乾燥成器。
那些石膏模是怎麼來的?靠便利店養著她留下了許多塑膠食器。平成二年出生的她幫這系列的作品起了一個有點時代感的名字——「平成食器」。日本人對於時間的詮釋,是語言,是食物,是樹葉的顏色,也是她越來越能理解的道理:外婆過世了,是人沒有了;然而感情結束了,但她還有土。
一切都和時間有關。
生活在緯度偏北的東京都,四季分明,日本人隨著節氣過日子,換季指的是什麼?指的是今天能買到的,明天就買不到了。夏天過去假期結束,氣溫劇降葉子轉黃或紅得掉落,她拖著行李回到那間在八王子的公寓裡,發現連超市都景色全非,買不到水蜜桃的她,突然不知道為什麼會自己一個人留在這裡。
一個人,住在離市區快一個小時車程的郊外,騎著一輛中古的腳踏車,後輪上有個輪胎鎖。租的公寓剛好位於一樓,裏頭有一張單人床、剛好能烤兩片吐司的小烤箱、常常忘了補貨而顯得空洞的冰箱和能剛好把身體完整容納的浴缸。簽合約交屋時,仲介提醒她不要把內衣褲晾在外頭,還是要防一下所謂的下著愛好者。會光臨此地按電鈴的不是村上春樹小說裡討人厭的NHK收費員就是網拍送貨的物流士,要裝作家裡沒人或是積極應門,這些應對都自有她的評判依據,總之,是少有真正的訪客。
她把各種奇怪的書藏在衣櫃裡,關於巫的研究、荒地上的野人、面具、埃及象形文字典、各地原住民的儀式和祭典。她總是忍不住對陌生人的好奇,對妹妹好奇,也對自己好奇。訪問獨立開店的女老闆和認真工作的自由人,迷戀認真的工作者就像迷戀認真工作的自己,透過說話和感覺,她用土作出不同形體的肖像寫生,在她感官全開的時候彷彿可以理解全部的為難,卻也讓人奇怪這些溫柔的好奇到底從何而來。
一五年的春天,她住進了那個什麼都沒有的房間,真的什麼都沒有。
搬入的當晚,她用搬家的紙箱做了一張桌子,用果凍的容器裝水來喝。
一八年的春天,她花了兩個禮拜把房間收拾好,把她的冰箱、她的洗衣機、她的烤箱、她的微波爐和她的單人床都包起來,然後告別了那個城市。
在獨居的三年裡,在那些不太需要說話的時候,她隨手把玩著一些看起來像該丟掉的垃圾。把網購留下的包裝紙攤平,畫上山的紋路。讓瓦愣紙屑互相排列組合建立關係,忽上忽下,若離若及。身體躺在堆疊枕頭的床上,手上畫下枕頭相依的起皺,透過自來水筆留下了不猶豫的筆觸。
是那一雙水裡來土裡去的手,每天工作結束,將所有的用具洗滌乾淨,反覆過水和泥土而乾燥而脫皮而發癢的手,同一雙手在睡前塗上乳液,剪短指甲。只要活著,她的手就會不斷的把土變成土條,把土變成泥漿,把土變成器,繞著圈刻上無以名狀的符號,用石頭打磨釉藥,將捏好的土器送入八百度一千度一千三百度窯裡,等待溫度上升,等待燒結,等待溫度下降,等待出窯。
時間總是等速的經過。
無論過了多久,她還是會和土一起,和自己一起,一起生活。
-
註
《聖山》(The Holy Mountain),亞歷山卓·尤杜洛斯基年代,1973。
《鼴鼠》(El Topo),亞歷山卓·尤杜洛斯基年代,1970。
《蒲公英》(タンポポ),伊丹十三,198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