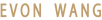|土與空氣的詩
秋天了,街道旁的台灣欒樹紛紛開花,從粉紅色漸轉紅褐色,收起一整個夏天的飽和色彩,在風裡變淡。我想起那個夏天,在陽明山上,我花很多時間跟自己唱歌,用手捏著各地的黏土,試圖留下那些被午後雷陣雨洗淨後的、特別清晰的山中色彩,留在陶製的空心之器。
那是座落於陽明山的「郊山友台」,被一片綠意包圍著的建築,幾棟老舊房舍錯落於樹林之間,穿梭其中有如進入龍貓裡的綠色隧道小迷宮,彷彿與世隔絕卻又緊鄰都會區,與市中心距離車程不到半小時。
幾棟屋子裡,有定期舉辦藝術活動的展覽空間、提供手作季節性甜點的「郊山食間」、以及擁有完整陶作設備的「雲森陶陶」工作室。這裡的夥伴們透過一系列關於土地共生、藝術工藝、食農文化及社區意識凝聚的實驗性策展和活動,尋找郊山生活深植於都市日常的可能,而我受邀與俄羅斯藝術家Maria舉辦一場名為「土與空氣的詩」的聯展。

我在展間後方的工作室裡駐村做陶一個多月。短租在台北東區的我,總是買好豆漿及三明治,轉搭著公車一路上山。在長時間移動的車途中透過耳機將一首首歌曲聽進皮膚裡,太陽的灼熱適合海洋的吉他、樹影的移動搭配古典樂鋼琴聲、天黑之後有夏夜晚風的口白,在工作室裡唱著從小聽著熟悉的那些歌詞,一個人捏著土。我刻意放棄自己的意圖,不畫草圖,隨手抓了塊土,幾乎不使用道具只以繞土條的方式,從底端慢慢往上一圈一圈的繞,手中的土有多少,作品就長成多高,長出非正圓形的有機形狀,淺意識地複製了室外藤架上剛結成的果實。

關於陶器,大多數的人會想到生活中各種拉坯製成的碗盤,用以承裝水、食物、植物的器皿,但早在萬年前人類就僅用雙手創造許多沒有承裝物體的空心之器,為了祭典、裝飾或是遊戲,我常常想,在缺乏承裝物件的實用性之外,這些器是為何而生?又存在著什麼精神層面的價值?
曾經在日本看著大雪中放置戶外的陶製大甕,什麼都沒裝,卻好像裝了所有的全部。還有一些空心陶製大甕埋在能劇的舞台底下、或著神社外的廣場地底,根據日本的漢文學者白川静先生對於「器」的解釋是:四個容器加上犬,犬為祭祀時之祭品牲畜。而其中的「口」指的是收集祭祀祝詞及盟誓的容器形狀。這些器往往放置於稱作「境界」的橋、洞穴、入口、階梯、島嶼、海邊、叢林、隧道等場域,空心之器雖無承裝物體的實用性,卻有著象徵內與外、生與死、此岸與彼岸、停止與移動等等的精神性。
這或許是為什麼在日本文化中,茶碗的地位與眾不同,茶碗就是置於境界的器,透過茶道的儀式性將實用之器昇華至精神體驗。在山中捏陶,使我終於置身境界,聞到泥土的味道。

特別炎熱的夏日,風中雲霧滿了就擠出雨,午後的暴雨總是毫不保留的下,濕濘泥土中探出的昆蟲是在都市中未能看見的色彩,我將塑形好的土胚放上轉臺,摸著土的濕度,用粉撲疊上各色泥漿,接著在土的表面刻下數字。特別記得有個下午,音樂反覆重播王家衛「墮落天使」中的那首忘記他,呢喃的粵語在雨聲中搖擺,我用力氣地刻下這一秒、下一秒,彷彿暗喻著我想你、忘記你,只是按照順序刻著數字,卻是充滿感情。心無旁騖地數著秒數、如同抄寫經文般將此刻的時間留在陶器上,無法由他人取代的筆觸,刻下自己內心最和諧的狀態。
這些日子裡,常常捏陶捏到天黑,和土長時間搏鬥的過程,換來全身痠痛與幾乎僵硬的雙手,但心卻是飽滿的,到現在都還記得用盡力氣後下山的車途中的踏實微笑。若是等不到公車下山,就找朋友來看夜景,工作室外的月光安靜而含蓄,但若是到另一頭文化大學的後山,夜晚才剛剛開始,伴著烤香腸的煙燻味望去的燈火絢爛感覺到整個台北市的年輕。
我的陶就在這樣的都市與山林間產出,如同一首土與空氣的詩,還記得展覽開幕當天的午後,陽明山下起一陣奇幻的太陽雨,使得展場的光與樹影被彩虹染上動人的顏色,作品佇立在展台,沐浴於森林浴中,光采奕奕。陶器表面起伏的數字如流水一般、也似土壤沈積,就像時間不能跳著走,卻也停不下來。岩石風化成土、土燒製成石,而作品總在數字堆疊至滿的那瞬間,它成為自己一個,一個獨立於我之外的回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