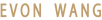|陶瓷的肖像計畫,東京的女老闆(一)
Cacao Mag 專欄|2021|圖文:Evon
「從對話到作品— 東京的女老闆們」
抽象的肖像雕塑會長什麼形狀 ?

八十公分高的尺寸,遠看像一座圓柱體的紀念碑,造型中段向內縮出女性姿態的曲線,表面是黑泥的粗糙質感,底部卻若隱若現地透出漸層的紅,細看整件作品佈滿手寫數字刻紋,直到頂端有個肚臍般大小的開口,旁邊謹慎用印壓下 Chen Chin Yu 幾個字母,這件作品,是我的「職務欄填寫__」從工業產品設計師,轉為一名做陶的學生之後,第一件公開展出的作品。

那是二零一六年的初夏,睡眼惺忪的平日六七點早晨,我擠在黑西裝沙丁魚罐頭的車廂中,時而墊起腳尖吸一口車廂頂層稍微新鮮的空氣,從大東京都最西邊的八王子市,搭上JR中央本線特快電車一路駛向東京。
滿載的列車上沒有空座位,通常我會卡位在第一節車廂,隔著玻璃窗看列車長的駕駛座迎來刺眼陽光,鐵道兩旁的紫陽花已結出小小密密的花苞等待梅雨季節的來臨,窗外的畫面從郊區的住宅快速刷過,進站又出站,刷過地下道再刷出隧道,終於展開一棟棟辦公大樓,我隨著行駛的節奏搖搖晃晃近一個小時,在東京車站下車轉乘,幾乎被擠到腳不落地也能順著人流前進,接著我逆著人流走進前往千葉的空蕩月台,繼續向著日升的那頭駛離東京,看著密集的辦公大樓換成一片片綠山,橫跨東京灣來到東邊的千葉縣。
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千葉,背著很大的背包,整路都反背在胸前用雙手捧著,背包裡面裝滿一間行動陶藝工作室所需的道具:筆記本,底片相機,輕便的塑膠轉盤,一瓶噴水器,一罐瓦斯槍,一把非常便宜的白色刮刀(因為有著恰當符合我作品曲線的切面成為我最不可或缺的道具,太心愛了,還特地貼了代替姓名貼紙使用的、亮粉色小花圖案紙膠帶)、濕紙巾、幾塊海綿,我的保溫瓶,最後是一個保鮮盒裝著溼潤的、新鮮的三公斤陶土。

對於一個平常出門只會將手機、鑰匙、錢包塞進口袋的,極度不愛帶包包的直男魂女子,如此這般捧著五公斤的大背包,搭乘兩個小時的特快列車,都是為了會見一位未曾謀面的老奶奶,為了我正進行的研究計畫。
當時我正就讀多摩美術大學的研究所,專攻陶瓷創作,我的同學們都是從多摩大學部讀完四年陶瓷工藝後進到研究所,秉持日本職人的精神延續自己從大二大三開始的技法創作,那時候的我只讀了一年關於材料實驗的課程,還在練習排窯與進窯,不但還沒找到獨特風格,老實說也沒有什麼特別想要說的話或極欲表現的題目。
於是在擬定研究計畫時,苦惱了好久,比起對於自己的在乎,我發現我對路人們更充滿好奇,尤其是對日本女性這個族群抱持興趣。

來日本之前,對日本文化的認知幾乎來自電視劇、電影及書籍,從以上媒介中架構出我對她們的想像,但在日本生活的這段日子,我認識了各年齡層,從事各職業的女性,打破我的刻板印象,才發現了在以男性觀點為主流的媒體中沒被介紹的,真實又好玩的日本女性。
平常在工作室玩土時,常常實驗各種做法用陶去表現,如鐵銹,如石頭等等不同的質感,有天突然想到「如果用陶瓷的質感,來表現人會是怎麼樣的呢?」、「抽象的肖像雕塑會長什麼形狀?」,「或許可以透過做陶來認識欣賞的女生?」,好多想法及可能性源源不絕的跑出來,於是當下便決定拿碩士的研究計畫來交朋友,訪問更多領域的女性,在對話的過程一邊進行陶作,最後透過作品表現我所看到的她,或許藉此能做出與他人、與環境有連結的作品,而且是只有我在日本讀書這段時間才能完成的作品,而我的研究計畫就定為「從對話到作品—-東京的女老闆們」。

「清玉很酷,妳應該訪問她」,綽號JJ的台灣女生,聽到我的研究計畫這樣跟我說,她口中的清玉其實是她奶奶,年輕時來日本讀書嫁給日本人,在千葉生活四十年養大了四名子女,如今小孩皆回台灣生活,反倒孫子孫女又來日本成為留學生,那天我和JJ約在千葉車站外的廣場,在一排鑄造成花生圖案的雕花鐵欄杆前碰面(據說日本國產花生有八成來自千葉縣),她要帶我去她奶奶以前經營的柏青哥店,一棟目前已經半荒廢佈滿綠藤植物的五層樓建物。
初次見面,陳清玉女士看起來與路上其他七十八歲的奶奶沒有區別,穿著不特別搶眼,但脖子繫著一條保暖且有點可愛的水藍色絲巾,帶著一頂遮陽帽,個頭嬌小,聲音也極小,聽到我是台灣人向我說了你好,轉頭就對著她好久不見的孫女一連串的問候與鬥嘴。
為了紀錄這最初的印象,我請奶奶站在鐵捲門前的雕花拱門,拿出我的相機,或許是底片機的快門聲喚起她的年輕時代,也或許是我按下快門前JJ把自己搶眼的塑料太陽眼鏡掛上奶奶的臉,清玉擺好姿勢突然成了極具氣勢的時髦奶奶,在我的膠卷映上她擁有一整棟樓的神氣,留下祖孫忘年笑鬧的身影,也走進一樓店面,在已成古董的遊戲機前拍進幾十年歲月盛衰的滄桑。

我們在一間堆滿雜物但還不至於積塵的辦公室中坐下,奶奶平常偶爾還是會來這邊,看午後電視的娛樂節目,終於我把背包卸下,稍微在辦公桌清出一小區擺上各種道具,以及那盒陶土,清玉其實不知道我的研究計畫想幹嘛,只覺得我的背包好像很重,她不知道我說要用陶做一個她是什麼意思,不過好像也不是很在意,自在地在她的小空間中,對我的各種提問作出簡短的回答。
「怎麼會開柏青哥店呢?」
「養家養小孩呀。」
「有什麼興趣喜好呢?」
「以前哪有自己的時間,就是拼命工作呀。」
在八零年代景氣正好之時,她從領時薪的打工仔頂下這整棟樓經營,樓下是柏青哥小鋼珠店,樓上是可泡湯休息的浴場,不知道是事情過了太久,再怎麼辛苦也都忘了如何描述,奶奶只用了日文的「一生懸命」四個字道盡她的青春歲月,彷彿空白了一大段人生,成為一顆專心為了他人付出的空心容器。
連他的孫女也是第一次,聽著奶奶說起年輕時瑣碎的記憶,我邊聽邊從保鮮盒中拔出拳頭大小的陶土,雙手搓揉來回拍打,將土整成長條狀,沒想太多就開始在包好報紙的轉盤上繞土條,我習慣由左至右逆時針的方向進行,土條繞完一圈之後繼續向上,奶奶說得越多,我繞得越高,她說這種店在日本叫「水商売」如同台灣俗稱的八大行業,她是當時這一帶唯一的女性經營者(她先生都忙著跟朋友下棋),常有小混混輸錢不爽,就拿小鋼珠的盤子當飛盤丟,但她完全不怕就再將盤子射回去。

果然奶奶是獅子座的,她說她正直做事沒有什麼好怕的,然後突然拿了桌邊花瓶中一大朵假蓮花說她是:「出淤泥而不染」,她喜歡黑色和紅色,喜歡的陶瓷是有繪圖的青花大花瓶,聽說她參加扶輪社的聚會時,會用心打扮穿上晚禮服,清玉令我想起我自己的奶奶,一輩子為家人付出卻難掩自己的魅力與光芒,丈夫幾年前過世了,她最近的興趣是上電腦課,七十六歲的時候第一次自己到夏威夷旅行。
奶奶口中沒什麼的人生故事實在太精彩,不知不覺我帶的土已經快用完,我想做一個空心卻有實體存在感的器,於是將土條繞至頂端,慢慢封起留下一個小開口,那天結束訪問後背包輕了不少,但手上卻多出一個需要小心呵護帶回工作室的雛形土胚。

接下來的幾天,在工作室裡看著未完成的土胚,不停回想談話的內容,小鋼珠、金錢、年歲,丁鈴噹啷反覆而累積,彷彿小鋼珠彈撞的聲音不絕於耳,直覺似的我開始在土胚上刻寫數字,從零開始一二三四五⋯⋯,就這樣老老實實地幫整個器給刻滿,刻完了覺得還不夠,還看不見清玉的拼命,感覺不到清玉的氣勢,於是我跑到窯廠,打開最大尺寸的窯門丈量窯裡的高度,決定要做一個當下能燒製出的最高尺寸,從底到頭刻滿數字看看能寫到多少,要用上黑與紅,要長成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態,是空心卻扎實、柔軟卻堅強的存在。

後來這件作品燒製完成,因系上老師的推薦獲得全額補助,於銀座藝廊舉辦我首次的個展,展覽邀請卡上是它的攝影照,我寄給奶奶後特別致電邀請她來看展,她依舊搞不清楚狀況地問我——那照片是我畫的圖嗎?直到她出現在藝廊,看見在展台上幾乎與她等高的作品,用佈滿皺紋的雙手、撫摸陶器表面數字的刻紋,她終於了解我做的是一生懸命工作的她,是不知道累、不計較得失的妻子與母親,是如今獨自生活而活得精彩的她。
事隔四年再回憶與清玉奶奶初次見面的這天,許多記憶已經遺忘,或著被我腦中反覆回想所建構出的細節所取代,但在挑選這些片段描述的同時,這些虛構成為更真實的影像,僅限於那個對話現場我所看見的陳清玉女士,很多人問我的作品為什麼刻數字,數字有什麼含義,其實重要的並不是表面的符號,而是我刻數字的那段過程,在平凡的日常努力工作著,放下大部分的自我,日復一日,用盡力氣,直到看見美,如同這件陶作一般靜靜佇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