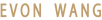exhibition|Floweret Rippling
展覽|花漾 |王怡方陶藝個展|2024|上海 與點 YUDINIST
訪談撰文|韓得昌


王怡方是一位茶人、陶藝作家、設計師、旅人、多元媒介藝術家、專欄作家、策展人。 根據她自己的說法,她是一個“做東西的人”。 可能由於她的背景是工業設計而非美術,使得她的創作更多具有一種易於親近的欣賞界面,觀者第一時間接收的是她糅合傳統和現代生活的感性,以及凝聚質地、觸感的手藝。


她用迎接春天的心情,來進行她的首次上海個展創作。 沒有來過上海的她,對這次的個展,醞釀了不少的期待,她採取一種很常見的方式,也就是透過其他創作者的作品來了解上海,尤其是——王家衛。 不過,為她帶來靈感的不是繁花,而是花樣年華。 原本目標是創造出對她來說專屬上海的作品,最終,跟著直覺的帶路,張曼玉穿著旗袍的模樣,和Cy Twombly的塗鴉畫風,成了「花漾-王怡方陶藝個展」的繆斯。
在她的首次上海個展前,與點對她進行了一次專訪,輕鬆討論了她對茶、陶藝、創作和對自己的感想,也簡單介紹了這次展出的作品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1. 請為我們介紹一下你做陶的方式:
我的陶作品是用手捏成形的,通常我會直覺的抓一把土,是多大就多大,用手捏出大概的形狀後,接著用美工刀這種簡單的工具,一刀一刀雕出比較 明確的形狀,其實很像在做雕塑。 我很喜歡木雕,而一般做雕塑是減法,做陶有趣的地方就在於陶土可以用加法也可以用減法處理,所以決定用這種方式來塑形,作為我個人主要的工作方式之一。
我會在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手法去削切、整修,雕出我想要的結果,作品上看得到像木雕般的斷面痕跡,就是這個修胚過程的顯現,也因此我傾向保留這些肌理 而僅在壺裡面上釉,素燒完花再更多時間再打磨。 顏色和質感也是我比較看重的,器物上大部分的顏色是在素燒後用小石頭慢慢把色粉磨進去,再燒過後可能再畫上一些符碼,進行最後的燒製來定色 。
我覺得我可以發揮的最大價值是在一件作品上花最多的時間,透過時間和手藝,把一小坨沒有價值的土,變成一個小小的寶物,這是一種很笨的方法, 很花時間不一定能成功,但每件作品會因此產生不同的個性,像是有機體般擁有自己的生命,這就是我做陶的方法。

2. 你最早是設計師、後來成為陶藝作家和茶人,對你來說,經歷這些身分的轉變,是否也產生了創作方式或想法的演變?
我在做工業設計的階段,追求的是量產的速度、效率、和降低成本,開始用手做陶後,好像開始反其道而行。 一開始做陶的時候,相當大的焦點也還在表現形式上,當逐漸形成自己做陶的方式之後,我發現自己對形體的追求降低了,開始減少自己的意識在其中的作用,越來越傾向基本的造形,觸感則成了更重要的事。
我發現自己一直在修胚和打磨,原因是我想在只有我跟土的相處時光中,把作品的每一寸肌膚都好好照顧到,找到壺捧在掌心最貼合的線條。 我和它長時間互動,使之成形,這個過程很像是一種物體式的日記,以一種曖昧和混沌的方式記錄了我想留下的東西,而這個過程也產生了勞動的作用,留下了我的痕跡,這個作用滲透到了作品的整體當中,作為器物之生命的一部分,留給真心喜愛這件器物的另一個人。


3. 你怎麼理解自己和陶藝以及茶的關係?
對我來說,陶藝像是和自己的對話,茶器是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的東西。 茶器是人和茶之間的橋樑,茶器給人的細微感受,包括質感、材料給人的直覺和上手的感覺是我看重的點。
我們需要接觸茶器才能體會到一杯茶的滋味,因此,茶器的上手時的接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,有些茶具看形像是普通的,但上手就會有感動,這是網路或圖片無法傳達的。 所以我在修胚的時候,就是在調整這種手感,因此我花最多時間的就是在雕琢器物的每一個細部。
另外我觀察到,光是茶具的顏色和訊息就可以帶來情緒的轉變,這也使我想回到比較單純的出發點,為器物帶來一些療癒的效果,透過在茶具上隱藏一些當代的和生活中的線索,例如BB Call時代的程式碼等等,為使用的人帶來一點驚喜,這個思考似乎和我的設計背景比較有關。 當我組織茶會或展覽時,則是回到了設計師或策展人的角色,來思考如何透過茶來連結人和人的關係。 因為茶具是靜態的,茶會可以用茶,透過時間軸把人和人、器、環境連結在一起,即使在歐洲做中國茶會也達到這樣的效果,這也是我最感激茶的地方。茶把這些這些不同的感受、思考和實踐連結在一起了。

4. 這次展覽除了茶具,你也帶來了具代表性的裝置作品,這些作品對你來說是什麼? 你覺得自己現在處於什麼樣的創作狀態?
我開始學陶時做的都是大型裝置,當時是有明確思路和要表達的概念的,然而經過作品反覆的塑形和燒製後,火和地心引力會產生不可控的力量,導致完好的造型坍陷或斷裂,也會使脆弱的成分變得堅硬,最終你會學會接受不可控,並且開始期待自己想像不到的結果。從最終作品的角度來看,我的陶因此產生了茶具和裝置的系統。
茶具的製作對我來說是明確且需遵循一定規範的,而裝置則是相對不可控且難預測的,就像我自己的生活有靜心和衝撞這兩極,我在做陶的時候也需要這兩種不同的創作出路來平衡。 裝置比較像是我自己的語言,但是一種混沌而抽象的語言,我需要這樣的管道來表達我的聲音,餵養持續嘗試和實驗的動力,而這方面的實驗結果,也能反饋到器物的製作上,因此在心理上和實際層面上都能形成比較好的平衡或循環。
「在這次展出的作品中,茶具是減法的雕刻手法,修胚下來的土去哪了?我調配成泥漿在土條上層層堆疊,用另一種循環再生的方式長出我自己無法控制的造型,這是我與土的對話,在互動中將落花的積泥長出新的模樣。」
做陶是一種不斷重複的工作,而每次的重複,卻能產生不同、甚至很有趣的結果,讓我對燒陶有越來越多的期待,這可能是讓我能繼續下去的動力來源。 這種不可預知性教導我的應該就是放下自我。對我來說,茶道的「道」大概就是去達到這樣的狀態,我自己在練字、做作品和泡茶的時候如果有練到這樣的心,作品就會比較好。

5. 據說你非常忙碌,目前是在拳擊、探戈和鋼琴三種興趣之間平均分配時間,還參與了各式各樣的活動,也經常旅行,這還沒有算上做陶和茶的時間,這是什麼樣的一種生活狀態呢?
我必須聲明,我做這些事情大都是在等開窯的時間做的(笑)。因為我從事的主要活動,做陶、寫字和行茶的狀態都是非常靜態的,我需要做一些相反的、具有衝撞性的事情來平衡我自己,我的陶是透過大量的手部活動來完成,這些興趣對我來說都是幫助我重新認識和運用自己身體的媒介,最終都還是會影響到我捏出來的東西。 旅行則是幫助我把創作的心態歸零,為下一次的系列或展覽,醞釀一個新的做陶的狀態。